“自從‘廣電21條’發布之后,我們的IP咨詢量提升了50%左右。”閱文集團版權業務總經理惠敏用一個數字直觀地告訴小娛,這一個多月以來,影視市場正在煥發新的活力。
對于很多創作者來說,這條政策像是打破沉寂的一聲鑼。
在過去的一兩年里,熒屏上熱鬧是熱鬧,卻也讓人有點疲憊。又是神仙談戀愛,又是千篇一律的女將軍人設,后宅那些嫡嫡庶庶還在爭斗,懸疑劇總愛留個爛尾。觀眾的槽點幾乎成了每部新劇播出時的“固定環節”。劇集不好看不是哪一類題材的錯,但一再透支信任的創作,卻讓觀眾的耐心越來越薄。
直到“廣電21條”的出現,行業似乎又有了方向感。
8月18日,廣電總局發布《進一步豐富電視大屏內容促進廣電視聽內容供給的若干舉措》。在電視劇司的解讀中,提出要壓縮涉案劇、現偶、古偶三大題材的立項比例,鼓勵更多現實題材和歷史題材作品。
消息一出,行業又熱鬧起來,它不是簡單地調控,更是在提醒整個行業:內容生態到了該重新洗牌的時候。長劇開機率下降,項目過會難度提升,原本的安全選項不再安全,新的題材和表達方式反而成了稀缺資源。
于是問題隨之而來:在“三大題材”退潮后,國產劇還能講什么?
現實題材看似站上主流,但它并非只有一種面孔;與此同時,喜劇、家庭、輕科幻、甚至夢核奇談等類型,也都在被重新審視。題材的競爭,正在從“誰有更多項目”,變成“誰能講得更真、更巧”。
娛樂資本論(id:yulezibenlun)借此找到了一些創作端與IP端的從業者,共同探討“廣電21條”背景下的題材重構之路:現實主義如何細分?類型劇如何突圍?政策收緊之后,新的空間又該從哪里打開?
#本文已采訪四位相關人士,他們也是「娛樂資本論」2025年采訪的第500-503位采訪對象
當“真實”成了最穩的底色,現實題材站上主流舞臺
“觀眾要的不多,只要不像在看假人說話。”這是創作者們近年的共同體會。現實題材的走紅,并不是因為它突然被政策加持,而是它最貼近真實的呼吸,最能讓觀眾在故事里認出自己。
二十四格文化傳媒創始人高金璽直言,“現實主義的界定,離不開明確的歷史時期,具體的時代背景是反映真實生活的前提,脫離這一語境,”現實“便失去了錨點。從本質上看,現實主義以還原生活本真為核心,既區別于玄幻、神話等依賴超現實元素的創作類型,也與那些違背生活邏輯、脫離大眾體驗的虛構內容劃清界限。”

流媒體影視時代,“現實題材”重新站上主流創作視線里,還是2017年首次提出網劇精品化,以及《人民的名義》成為全民爆款的時候。當時鄭曉龍對“現實題材”與“現實主義”做出過一種解釋:“現實題材”是一種題材,“現實主義”是一種表現手法,也就是“講什么”和“怎么講”的區別,前者是題材維度,后者是創作態度。
在與高金璽聊到現實題材方法論的時候,他提到了二十四格文化傳媒在兩年前播出的爆款劇《風吹半夏》,故事之所以能夠成立,是因為它牢牢扎根于“1992年至2002年的社會語境”,那時候正是中國改革開放進入到第二個十年的階段,機會多,是“站在風口上,豬都能飛”的年代,但同時鋼材市場的起起落落、民營企業的磕磕絆絆,這種“真實的復雜性”,自帶類似“魔幻”的張力,不是超現實的奇幻,而是時代轉型期特有的矛盾感、戲劇性,恰恰為劇作的戲劇沖突提供了扎實的現實根基。
而后來高金璽在處理《多喜一家人》時,則將初版劇本中過于理想化的“溫情合家歡”逐漸調整為一家人拆遷暴富后撕開表面“你好我好”的和平局面,直面家庭利益撕裂后現實的沖突。“生活中不該只有’掛在墻上的家和萬事興’,像拆遷后‘分錢不均’這樣的利益沖突,是很多家庭在現實壓力下的典型困境。”他認為正因為敢于把真實的欲望和矛盾放到臺前,作品才真正有了扎根生活的真實感。
簡而言之,現實題材不是擺出一副正經面孔,而是能否讓觀眾認出生活里的痛感與笑聲。

新力量文化總經理黎永杰在融合了“新京味”與“公路片”風格的當代都市劇《漂洋過海來送你》中,選擇用輕松幽默的方式去描摹生活的真相。劇中講述北京胡同青年那豆為追查爺爺骨灰被誤換的真相,踏上一段荒誕又動人的尋灰之旅。故事以小人物的視角串聯大時代的記憶,折射出社會變遷,讓“笑”與“淚”在故事中交織。
“如果說我們選擇做這種現實主義題材,又不想做得特別嚴肅,特別沉重,還是有多種方式去呈現這種類型化的表達。”黎永杰希望用更輕盈的語態去抵達真實。現實題材在他看來,不一定非要沉重,它可以是荒誕的、溫情的,也可以是帶著一點諷刺和一絲浪漫的。
這部劇正是以輕松幽默的方式捕捉生活的復雜氣息,荒誕之下有溫情,笑聲背后是淚意。它既不回避生活的荒唐,也不吝惜生活的溫柔,在“尋灰”的路上呈現了一場帶著煙火氣的平民史詩。
前不久播出了迷霧劇場口碑懸疑劇《目之所及》的承皓影視,其創始人巫天旭在談論如何創作高質量項目時就提及創新性的重要,他所謂的創新并非停留在設定層面,特殊的身份、極端的劇情,只是故事的外殼,真正的“新”,一定要從現實里來。
比如《目之所及》從類型上說是懸疑劇,但真正打動人的,是母女關系、家庭隔閡與和解。這種“情感落地”的現實基因,才是作品與市場區隔的最大武器。

觀眾所謂的新鮮感,其實來自于在真實的土壤里長出的稀缺角度。
如果說高金璽強調了現實題材與現實主義的區分,黎永杰展示了輕松與幽默的可能,那么巫天旭則是強調了,無論題材形態是什么,現實關照才是所有創新的根基。三種思路的核心只有一點,現實題材之所以成為最穩的底色,不僅因為它順應政策導向,更因為它能不斷被細分和重組,形成不同的表達方式。
在今天,“真實”已經不是一個標簽,而是國產劇最堅實的收視密碼。觀眾會為荒誕發笑,也會為矛盾落淚,但歸根結底,他們愿意為真實買單。

AI作圖 by娛樂資本論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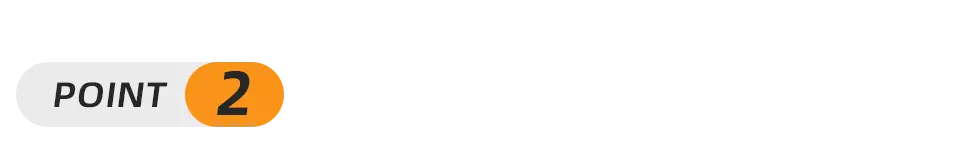
觀眾的“新口味”要從哪些題材長出來?
現實題材固然是當下最穩的底色,但觀眾不會滿足于一種口味。正如黎永杰表示,“三大題材作為市場主賽道,具備較成熟的商業化轉化基礎。而對于文學性較強的精品內容或創新性題材的探索項目,鑒于其孵化周期較長,我們會以內容質量為核心,在保障收支平衡的前提下給予充分創作空間與時間,實現藝術價值與市場潛力的有效結合。”
主賽道固然重要,但無論是創作者自己的熱愛與喜好,還是觀眾期待的新鮮與驚喜,都會來自那些還未被充分開發的題材。
喜劇就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突破口。近年來,平臺在喜劇賽道動作頻頻,不管是愛奇藝的“小逗劇場”還是騰訊視頻的“板凳單元”,囊括從都市生活到古裝合家歡的多種子類型。

愛奇藝推出《破事精英》《瓦舍江湖》《少爺和我》《大王別慌張》,騰訊視頻推出《蘭閨喜事》《萬春逗笑社》《請和搞笑的我談戀愛》等,嘗試讓喜劇在多種語境里切換。尤其《鵲刀門傳奇》以東北喜劇融合武俠元素為切入,既保留“笑料”又植入現實生活細節,被認為是“武林情景喜劇”的一種新嘗試。
這表明平臺層面對喜劇題材的重視,正從單一的“陪襯”角色,向一種可能承擔情緒調節與現實關照的方向邁進。
喜劇從來不只是調劑,它是另一種討論現實的可能。從一代人的《我愛我家》《編輯部的故事》,到一代人的《家有兒女》《武林外傳》,影視行業或許欠了現在這一代觀眾一部全民喜劇。
少兒和家庭類題材,也正在成為被重新看見的方向。觀眾大屏化的觀看習慣,讓“全家能坐下來一起看”的劇再次有了價值。
黎永杰就提到,“我們現在的劇集市場中沒有適合全家人一起看的劇,現在大家看劇都是各看各的。”新力量正是看到了市場上這種題材的空缺,由其開發制作的待播劇《牧星戰隊》,就是這樣一部適合家長帶著孩子一起觀看的電視劇。

確實“合家歡劇”越來越稀缺,而類似《歡樂家長群》《米小圈上學記》這樣的嘗試,正是重新滿足大屏環境中家庭共看的需求。它們的優勢在于,不止能觸動家長的教育焦慮,也能兼顧孩子的代入感,從而形成更穩定的受眾群。
換句話說,家庭和少兒題材,是在內容供給側收縮的背景下,自然浮現出的補位選項,尤其是在廣電不斷提出“豐富大屏內容”后,這類合家歡劇更方便滿足客廳用戶需求。
類型不是問題,問題是有沒有現實的支撐。

高金璽也提醒,題材的選擇絕不是為了跟風,更不能成為“吃人血饅頭”的生意。他強調,現實題材的真正價值在于對社會語境的把握,而不是單純蹭熱點或者復制成功模式,正因如此,《風吹半夏》才會立得住。
從喜劇到家庭少兒,從輕科幻到類型融合,觀眾的“新口味”并不是憑空生長的,而是在舊賽道讓位后,新的表達方式自然長出來。現實題材的穩固,讓行業有了底氣,而這些新方向,則讓國產劇在政策和市場之間找到更多元的出口。
觀眾不會拒絕熟悉的類型,但他們一定需要新的打開方式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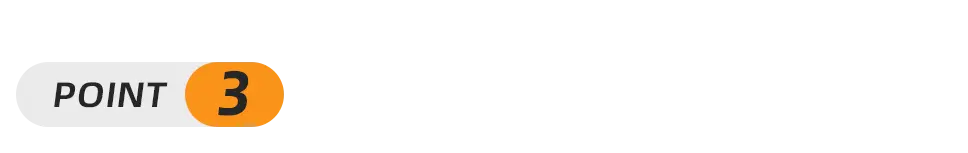
題材格局正在從源頭改寫
題材格局的變化,最終會落實到源頭環節。過去幾年,行業習慣了“買頭部IP、押主流題材”的邏輯,晉江的古偶、起點的古裝男頻女頻、甚至豆瓣閱讀的懸疑與女性文學,都曾是公司必爭的資源。但在“廣電21條”提出壓縮涉案、現偶、古偶的背景下,單純依賴舊有賽道的開發已不再是穩妥選項。
這意味著,IP開發和劇本孵化的方式正在發生根本性轉向。比如,豆瓣閱讀出圈的多部作品,往往帶有濃厚的現實主義氣質,從家庭矛盾、女性成長,到社會議題,都具備與政策和觀眾需求同步的潛力;知乎鹽言故事則不斷產出“鹽言三絕”,類型上從早期的虐戀古偶逐漸轉向志怪、大女主和懸疑,說明市場本身已經在通過讀者的選擇對題材做篩選。
與之相比,晉江的古偶、現偶IP依舊有體量優勢,但如何在孵化過程中賦予作品現實關照,成了公司和創作者必須解答的問題。
惠敏向小娛提出了閱文IP中“現實+”的邏輯,如今現實題材已經不再是單一的當代社會故事,而成為所有創作的底層母體,她認為“現實+”的復合類型構成了更具創造力的內容源頭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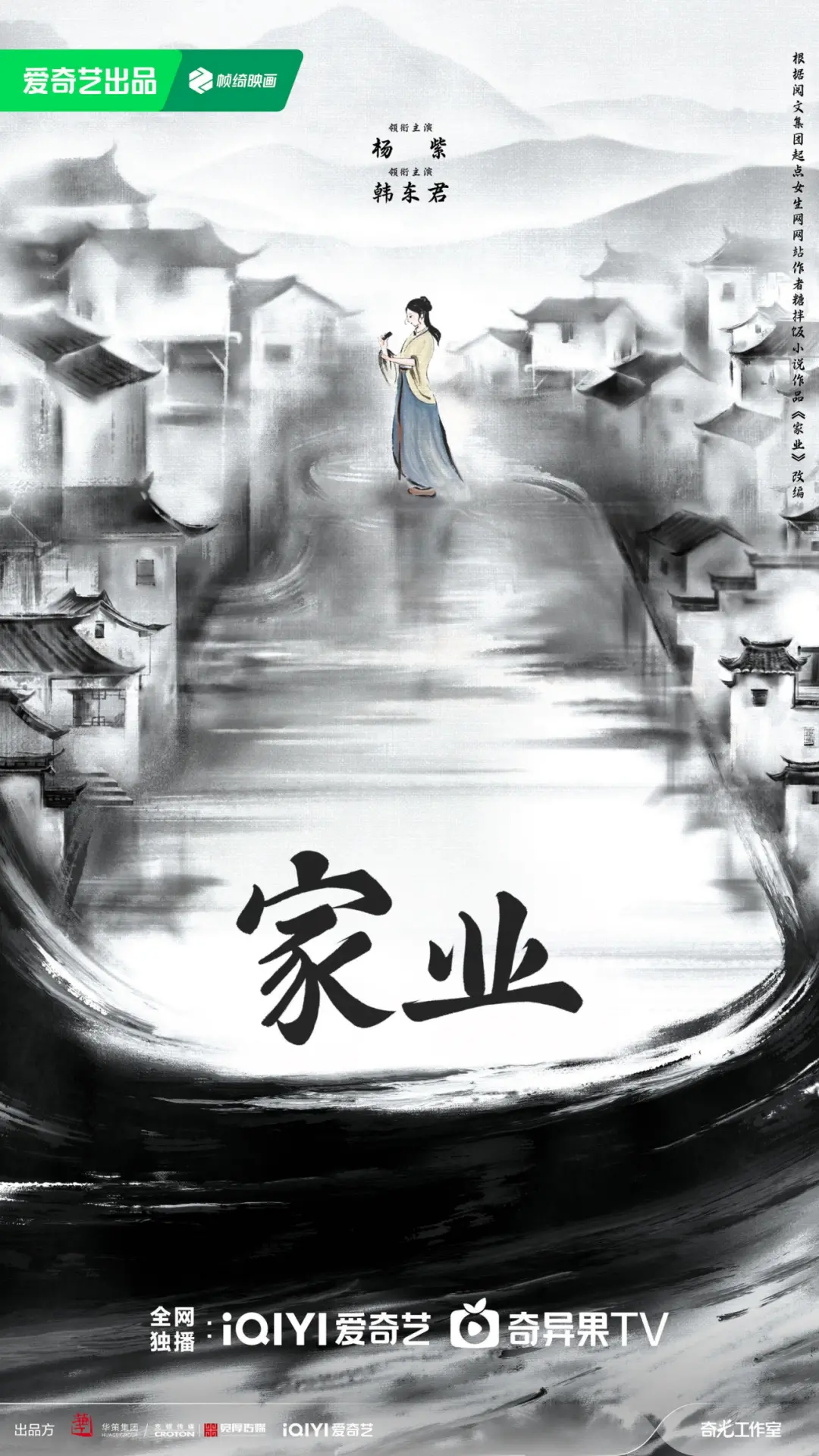
比如“現實+科幻”的《剖天》,以父子身份錯位講述人性的循環與救贖;“現實+奇幻”的《野鹿便利店》,用奇幻設定包裹職場壓力與治愈主題;“現實+傳統文化”的《家業》《驚山月》,將非遺中的徽墨、制香等傳統工藝融入當代敘事,展現文化傳承;女頻也正在從偶像敘事轉為“現實+女性成長”的敘事。
與此同時,惠敏在關于題材創新方面也表示,網文的題材更新速度往往具備領先性和引導性,所以閱文內部有不少創新題材的IP也長期受到影視同行的關注。
比如前兩年全網現象級的《道詭異仙》,將流行的幻想元素與中國傳統文化結合起來,既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文化內核,又有讓人眼前一亮的新穎世界觀。
最近《道詭異仙》作者狐尾的筆又推出了爆款新作《舊域怪誕》,講述主角重返童年,表面上是熟悉的九零年代,但在主角成年人的視角里,童年世界充滿了詭異的規則,比如少年宮是一個有生命的龐然大物,變成大人就無法開心,這是一個必須嚴格遵守規則才能存活的超現實世界,而違反規則的懲罰是疼痛甚至陷入魔幻。為了擺脫規則獲得自由,主角在這個似是而非的世界里開始探險,挑戰詭異規則,展開成長與治愈之旅。整部作品將“規則怪談”的創新設定與年代懷舊結合起來,形成了獨特的“中式夢核”。

這種創新不僅出現在文本端,也正在影響改編邏輯。過去,影視公司更傾向于改編結構穩定、篇幅完整的頭部小說;如今,在“廣電21條”導向下,一批“難改”的作品反而迎來機會。
惠敏舉例,《從姑獲鳥開始》這樣單元結構的故事過去被認為篇章復雜,且每個單元風格差異較大,按常規項目開發的話,壓力較大。但現在可以開發成系列化的短劇集,每個單元8至10集,更適合當下觀眾的觀看習慣。同時,將總成本分攤至各單元的模式,也讓項目的整體財務結構更為健康。
此外,在歷史題材的回歸上,惠敏也談到,“大家不再總把鏡頭對準帝王將相,反而可以聚焦大時代里的小人物。小人物的命運是大歷史的‘毛細血管’,他們的悲歡、選擇,反而能讓觀眾更有代入感,既有歷史題材的縱深感,又有人間煙火氣。”
作為閱文擅長的賽道,《唐人的餐桌》《五代風華》《狀元郎》這些影視公司重點關注的IP,都是在找歷史與當下的連接點,歷史題材不是要改寫原貌,而是要更貼近現代觀眾的視角解讀歷史。

因此,國產劇題材的未來不只在于“拍什么”,更在于“如何孵化”。當源頭環節真正完成一次結構調整,從“現實+”的內容創新,到網文前置孵化的成熟,再到政策導向下的新類型開放,實現現實題材的穩固、多元賽道的興起,才有可能形成持續的內容供給。
題材的變動看似是比例問題,實則是創作生態的重寫。“廣電21條”的出臺,不只是一次內容調控,更是一場行業生態的自我凈化與再分配。它讓創作者重新思考題材與社會的關系,讓市場回到“故事從生活中來”的原點。
從這一刻起,內容的生長方向,不再取決于誰能踩中風口,而在于誰能在“現實”的土壤上種出新的想象力。真正的紅利,不是某個題材的爆發,而是創作者重新獲得與時代共振的勇氣。
- 1024程序員節京東開放“零幀起手”數字人技術
- 2025廣州車展一汽-大眾油電并進,以科技賦能開啟全新商品布局篇章
- 全新豐田威蘭達實拍!外觀顏值升級,配置拉滿,提供三種動力
- 20余款車型版本,9.98萬元起價,2026款長城炮廣州車展上新
- 全新保時捷911 Turbo S:賽道性能與豪華舒適完美平衡的杰作
- 全新一代奔馳GLB低偽裝諜照曝光,外觀向Smart精靈#5靠攏
- 古天樂香港提極氪009新車,現場兩“雕兄”惹眼
- 智界S7亮相廣州車展,20萬級智慧轎車再樹標桿
- 廣州車展 | 長安啟源Q05上市,起售價7.99萬,十萬內唯一激光雷達純電SUV
- 華為科技+改裝神器,猛士M817 Hero版硬核上市
- 五菱星光家族三星亮相天津,全能舒享大7座引領家用MPV新體驗
- realme真我P4X 5G手機參數曝光,配置亮點多
- 2025中國5G+工業互聯網大會丨我國衛星物聯網業務商用試驗正式啟動
- Galaxy A77手機跑分亮相,三星時隔3年有望重啟A7x系列
- 蘋果又一新品上架,498 元
- 鄂湘贛企業之間有望實現“一鍵接單”
- 村民合力“扛”上萬斤木樓平移 “硬核搬家”怎么做到的?
- 三屆全運金牌榜首!山東憑啥這么牛?
- 全球首款2nm手機芯片!三星Exynos 2600采購價比高通驍龍8E5還便宜
- 拼多多的錢都花到了哪里?